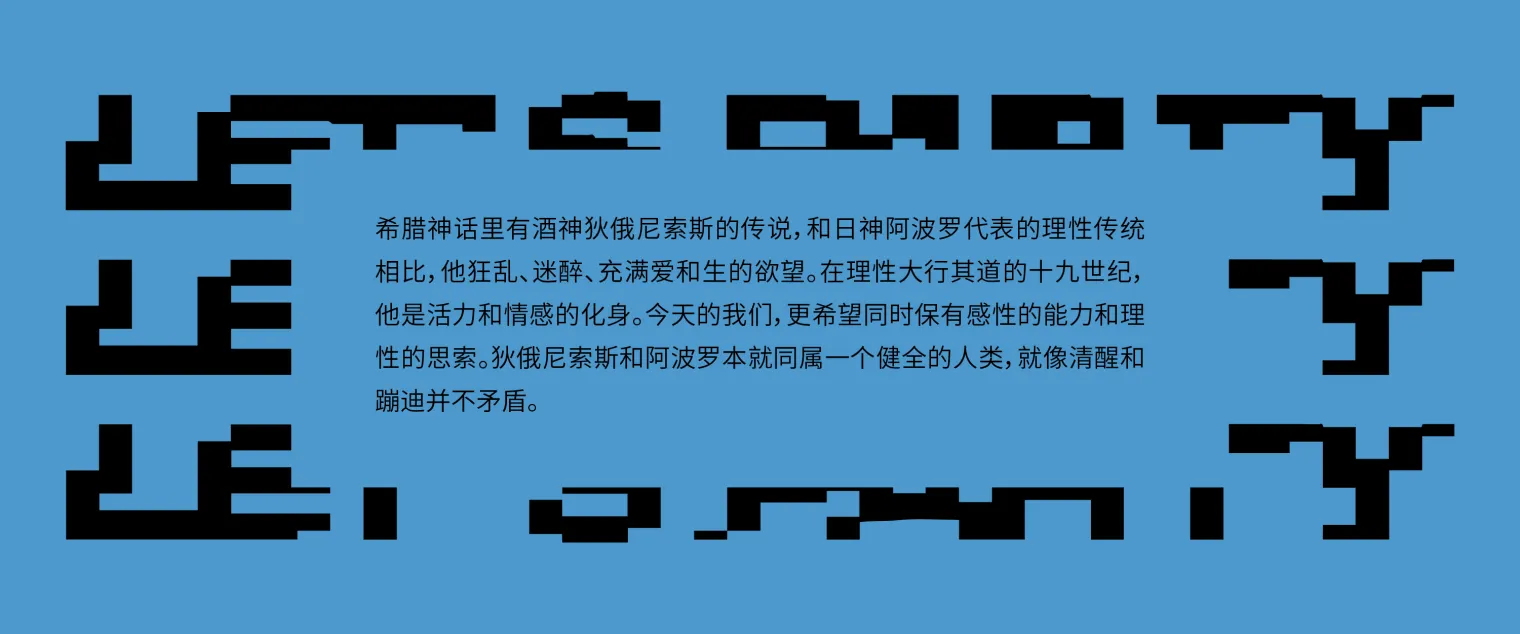放下耻感后,我在短剧剧名中获得了巨大快乐丨清醒蹦迪

虽然不是短剧观众,但互联网世界有时候就是,一件事火到一定程度,哪怕并非受众也会被信息的浪潮沾湿裤脚。短剧的浪,就这么汹涌地扑到了我的脚边眼前。
我也确实被吸引了,但并不是因为点开了某部剧。在看剧之前,那些长得惊人、画风清奇、情节费解的剧名就足够抓住眼睛了。
虽然长剧也不乏一些莫名又烫嘴的长名字,但全然没有短剧剧名那种“快准狠”的感觉。短剧的名字,和它们的剧情一样,总是能精确踩中你的好奇点。有些名字,哪怕你看罢并不会立马点开,但它的情节已经留在脑海里。
不过,相信一部分人不看短剧的原因,也是直接被名字劝退。
《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母凭子贵后被老板全家宠上天》《重生主妇黑化实录》《让你送外卖,你摘下高岭之花》……当你想亲口念出这些剧名时,作为社会人的理性面会努力试图捂住你的嘴,换言之,会有种莫名的羞耻感。

这恐怕是为什么即使在新闻和数据里,短剧火得一塌糊涂,但除了那部送话题女王咪蒙“熹妃回宫”的《黑莲花上位手册》和在春节档让短剧“弯道超车”的《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外,我们很少看到短剧在公众层面掀起大范围讨论——看短剧,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件有点儿私密的事。我们一方面享受着它提供的情绪多巴胺,在小人物的迅速逆袭、受气包的觉醒翻盘、霸总的无底线专宠和女王的无上权谋中体会人生的超绝爽快,另一方面却羞于和别人分享:“我最近在看一部剧,叫《少帅你老婆又跑了》,超好看!”
和还是要讲究些艺术性和视听语言追求的长剧不同(当然,也不乏不讲究的长剧),短剧的诞生更具草根性,“土生土长”的气质似乎决定了它们并不需要遵循长剧创作的那套逻辑,甚至相反的,脱胎于碎片化内容创作的短剧,其核心逻辑是内容找人,要在汹涌的信息洪流中抢夺大众的注意力,“一眼悚动”的标题党式剧名是最有效的。
足够的信息量和爆点,是人们打开内容的第一个钩子。
不过,短剧的剧名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放飞的。
2020年底,当短剧刚刚走出野蛮生长的用户自制阶段,进入探索自身商业模式的成长初期时,影视制片人及导演添翼便开始尝试竖屏短剧制作,是较早一批涉猎短剧的专业从业者。
“我们那会儿名字还不是这样”,他回忆。比如他自己执导的《胡同儿》(2022年播出),还有快手2020年出品的爆款短剧《这个男主有点冷》,以及当年大火的《浮生当铺》《奇妙博物馆》等,仅从名字上看,和我们熟悉的长剧命名方式没有太大差别。

转变大致出现在2022到2023年间,短剧完成了付费模式的探索,进入一个爆发增长的阶段。有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付费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用户规模超过2亿。巨大的市场规模既带来了更多的机会,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夺得更多的关注,自然需要更亮眼的名字。
我们最为熟悉的短剧风命名,一个最显性直观的特点,就是它往往很像一句话,只看标题,已经能够对剧集内容和最大爽点有个初步认识。剩下的就看你是喜欢《王府继兄宠我如宝,亲哥却后悔了》这样的打脸式爽快,抑或《离婚后我成了全球首富的外孙女》这种先抑后扬的上位式爽快,还是《认亲后,误入帮派成团宠》这样全世界都爱我的爽快,以及《觉醒当天,我当上全国状元》的逆袭即巅峰的爽快。
添翼看来,这种“故事梗概式”的命名方式是很好的“宣传物料”:“它就是通过一句话让观众知道能看到什么。”他说,给剧集起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放在互联网世界,它又可以不那么“严肃”。当作品量呈井喷式增长,面对更快的制作节奏和更多的观众,一个“所看即所得”的简单粗暴的名字,能降低大众的理解门槛,帮助他们快速决策。这在添翼看来不失为一种聪明的商业做法,“有的片方可能一个月要出10部作品,(所以)在起名这件事上真的就没法特别在意”。

2023年,红果平台的上线,更是给取名这件事提供了算法加持。和优爱腾等传统视频平台的“推荐模式”不同,红果背靠大数据,基于自身的算法给客户进行针对性的内容推送——如果你搜索过一次“重生”,或者点开过某个“偷听心声”相关的内容,那么接下来你就会收到很多类似的短剧推荐。机制和你刷小视频一样。这种情况下,一旦某个剧火了,就可能出现相似的名字和主题扎堆出现的情况。
但是,没关系,短剧的奥义就在于,即使相同的主题,但用上不一样的(邪门儿)配方,总能给初入这个世界的你亿点点震撼。
拿大热的“重生”剧来说。有的重来一遍忙着搞钱,但只是致富不够有吸引力,必得搭配点其他元素,比如“重回1990:带女儿和小姨子致富”“重生九零年代:拯救难产媳妇后发大财”。也有在获得人生第二次机会后,积极修正前世错误的,而这个“错误”千奇百怪,像《回家的诱惑》和《请和我老公结婚》这种惩治渣男的设定,放在短剧堆里,就太寻常了(当然,也很主流,痛打渣男还是“爽中爽”)——“重生当然要先去救落水总裁”“重生:逼着社会老爸金盆洗手”“重活一世,我再也不当后爸”……更普遍的,在重生后花式脱胎换骨走上各自的人生巅峰,有的“不再原谅”,有的“强得可怕”,有的“嫁给知青让前夫后悔”,有的“拿捏全家”,还有的“科技兴邦全靠我”……

对于一个只在刷微博时看过推广片段的人来说,打开短剧平台的那一刻,有种翻开“e世界故事会”的感觉——扫过五花八门的标题,纵然主题有不少雷同,但又各有各的刁钻细分领域。光是浏览这些剧名,感慨于“到底是什么脑子想出这些奇形怪状的剧情”时,已足够大开眼界了。
不得不说,这种极具风格的命名方式,正中人类猎奇心理的红心,甭管看上去设定多离谱——正是因为离了个大谱,人们才更有打开的冲动,要亲眼瞅瞅这葫芦里到底作的是什么妖。它们就像那个最会讲八卦的朋友,神神秘秘凑到你面前丢下一句“你知道吗,隔壁秦阿姨昨天自爆身份给她儿媳撑腰!”(短剧《老妈报身份替儿媳撑腰》),你忍不住就会跟一句“怎么个事儿?展开讲讲”。
人类爱说“好奇害死猫”,而在猫的眼里,或许我们这些人类才是真的要被八卦之心“害死”。
作为一种文化产品,“low”似乎是伴随着“爽”,贴在短剧身上难以去除的标签(即使它们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升级)。可是,明知剧情没营养、没深度,明知从名字开始,短剧就在通过频密的“钩子”,引着你一集一集、一部一部追,但就是控制不住手指一下一下地刷下去。其上头程度,即使手握诺贝尔奖,莫言也得“强忍欲望”才能戒断。
于是,伴随着这个市场的不断扩大,人们也反复追问:面对短剧,我们怎么就那么“口嫌体正”?

当然还是因为“爽”,但更重要的,是“高效”。在信息愈发碎片化、时间越发不够用的时代,短剧的精悍体量让你在通勤路上便能看完主角从受欺负到扬眉吐气的全过程,不似追长剧,苦哈哈熬过大半部剧,可能要抑郁半个月才能看到一点希望。这样的百转千回,对讲求效率的当代人来说,真的太久了。谁想上班的时候胸口还为主角的遭遇堵着一口气啊?
说到底,刷短剧的诉求和看电影、追长剧不一样。就像添翼所说,“高级”的商业大片和短剧,本质都是制造爽感,只是各有侧重。当人们想感受极致的视听享受,会走进电影院看F1,而如果我只想不动脑子地打发一下碎片时间,获得片刻的精神快乐,短剧无疑提供了新的选择。
其次,更短的制作周期决定了短剧能够更快地回应大众的情绪诉求。在毕业致辞中“自爆”沉迷短剧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汤拥华就发现“短剧的很多创作规律,其实不是剧组拍出来的,而是观众评论出来的”——一旦观众开始吐槽某些套路,创作者们便会减少相关剧情,转而拍摄大家更爱看、讨论度更高的内容。相应的,一些小有名气的演员,也会将粉丝的期待考虑在内。粉丝想看他们演什么类型的角色,他们便会尝试寻找合适的内容。

这种“双向奔赴”让人们更容易在短剧里获得情绪共鸣,不管你是想看甜甜浪漫爱,还是潇洒事业脑,甚至更奇巧的设定和角色,海量的短剧中,总有对你此刻胃口的。
反观长剧,由于制作时间更长,还可能出现被压着无法播出的情况,以至于一些剧作在拍摄时可能还符合当时的社会语境,但上映之时里面的桥段可能已落后于主流叙事。
最后,再回到短剧的名字。作为一部剧的最简略梗概,它们提炼了每部剧最核心的内容,也变相以最精简的形式,将时下流行的文化、主流的情绪、多元的世界观和欲望,像书籍目录一样列在你面前,肤浅浮夸,却又有另一种真实——我们对某种极致感受的想象和追求——生活很纠结难顶,还不能做做穿越后变身满级王者的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