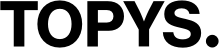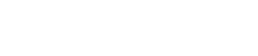除了大碴子味喜剧人,东北还有啥?| 城南唠嗑

有过易地而居经验的人可能都明白,在他乡,最害怕的事是与人探讨自己和家乡的关系,最喜欢的是为家乡撕标签。
前者因为立场的摇摆——如果对故土乡情足够热忱,恐怕解释不了自己远走的动机,要说没有一丝怀恋,恐怕也显得你这个人太过冷血,而且多半也并非事实。无论如何,你生活过的土地总在你身上留下印迹,与你的意识或潜意识藕断丝连,快刀斩乱麻固然痛快,过后难免觉得失去了一些注解自身的有力论据。
后者就单纯的多,你先天占据事实论据的优势,能想出一百个故事驳斥或佐证一个简化认知的标签,心中底气充足,嘴上语似箭簇。
但这两者实际上指向同一个动作——重新审视一片土地,一片你曾经熟悉的地方,说出点不一样的东西,让自己和他人都和这里更贴近一点,对它的现实看得更仔细一点。
城南唠嗑之「城市群像」系列就立足于这一简单逻辑,我们选择了几个地区/城市,希望通过和当地人或对沉浸式地在当地生活过的人的观察、交谈,对既有的标签做拆解和挖掘。我们希望它有趣、有料、有温度,更希望它可能化解某些失去弹性的交流模式,化解某些偏见,为理解问题的深入性和多面性提供一点小小的参考。
「城市群像」第一次开聊,我们选择了东北和刚刚做为特邀主编之一、与一众脱口秀演员合作了《喜剧的秘密》一书的贾行家,聊一聊东北的三个标签:喜剧、文艺复兴、衰落或变形。贾行家老师自称是个非典型的东北人,但他对东北喜剧和喜剧人的理解、对东北的社会交往模式和典型东北人气质的观察,其实精到而独特。
贾行家小传:自谦为“一个东北来的写作者,写些有人需要的东西”,因为“对语言感兴趣”,从小喜欢和留意喜剧的语言和表演形式。实为《单读PLUS 喜剧的秘密:从脱口秀说起》特邀主编,网易博客”阿莱夫“作者,出版作品《尘土》《潦草》。
建议:
文字为概括,播放键里藏着更多有趣内容。
音频使用指南:
下饭、摸鱼、通勤、下厨、躺在床上将要入睡还未睡着的,各种过渡场景都适用。(听音频,点这里)

#东北的喜剧气质
TOPYS:你是怎么对喜剧产生兴趣的,你认为和你是东北人有关系吗?
贾行家:我觉得可能和我是一个在80年代听着电台长大的北方人是有关系,是不是东北人这个事情可能关系不太大。我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潜台词,大家伙会觉得东北人就比较逗,是吧?
大家觉得二人转气质是东北人的一个共性,其实我对二人转是完全没有什么感应的,我对喜剧的接触就是和整个的北方人民一样,要不是在电视上看,从春晚,或者是什么曲苑杂坛这些节目里面的曲艺,要不就是听相声,这个是我所接触到的喜剧。
大家印象中是那种喜剧语感的东北人,我也挺喜欢的,但是我事实上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才接触到那种类型的东北人。我在哈尔滨上大学,会来一些黑龙江其他市县的同学,有些地方的人说话特别逗,他们是互相逗话逗出来的。
东北话,尤其好像一个省的人,他们的口音就是变化比较平缓,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但是如果是本地人,是听得出来你是哪个县的,不同地方的人说话会很好玩,都有自己的喜剧和幽默。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已经不是一个养成的阶段了,我是在观察。这可能是因为我对语言比较感兴趣,我会对他们的表述留意一些。但事实上我所谓的喜剧经验就和那一代人是一模一样的,像我们这次做《喜剧的秘密》这本书,去和这些脱口秀演员聊的时候发现,大家的喜剧基础都差不多,关键是你在哪个年龄段长大,而不是你生活在什么地方。
TOPYS:近二三十年,东北方言作为喜剧的重要元素被不断利用、翻新、再利用,甚至喜剧成为东北的一个显著标签,你觉得东北方言和喜剧的“捆绑关系”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东北话更容易逗人发笑?
贾行家:首先就是普通话的传播造成了很多的方言里面的幽默是没法被大多数人理解的。你比方说粤语里面有很多幽默,你不通晓这个语言,你没法理解。但好像东北话只有喜欢不喜欢,没有听懂听不懂。
现在喜剧的要求是要以普通话为母语,才能够顺畅地表达一个有感染力的喜剧。这个就把好多人挡在了外面,南方人处理普通话的时候,他也是在处理一个非母语的语言。
好多作家都有这种抱怨,比方说,有位老师在讨论毕飞宇的时候就说到这件事儿,好多南方作家他更善于处理的、更有感觉的是他的母语。但是这个母语写到书面上,北方的编辑,甚至国家的语言规范都不认你,所以他们要反反复复地去把自己的方言的感觉迁移到普通话里。
但作为东北人,我们是也移民,我们说的大体上是普通话。辽宁话是更可爱的,它在方言音调上增加了一些喜感,同时并不影响你理解,所以好的喜剧演员出在辽宁的多,也有这个因素。我觉得口音是决定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可能是生活方式,东北人挺愿意表达的。很多人都分析过,一方面是说东北冬天长,大家农闲凑在一起说话的时间长,生活方式里面给你提供了这么一个基础,这一冬天大雪封山,出不了村子,就在村子里头互相逗话。还有可能跟工厂的聚集文化有关,就是一个人他很逗、能够让别人的话不落地,去把正常的表达发挥成一个笑料, 或者能够用一个出其不意的方式损到别人,给别人一点刺激,其实是一种隐形的权力,这种东西也在激励大家表达。
我的观察的话,有一个原因就是东北的人际关系比较扁平。东北没有那么强的宗族观念,谁都可以说说笑话,老丈人和女婿像密友一样,互相开黄色玩笑都是完全可以的,我想在山东、在福建、在潮汕地区好像是不应该出现这样的事情的。

TOPYS:很多人认为东北人天生有幽默细胞,你在生活中是个会“逗”的人吗?也有人说比较热情、会自来熟是东北人的典型气质,是这样吗?
贾行家:从来没人说过我逗,有很多人说我没有所谓的典型的东北人气质。首先我不认为“东北人气质”不好,但我的确也没有那么强的对家乡的自豪感,同时我也没有那么强对家乡的痛苦或怀恋,我会觉得我和我长大这个地方是有距离感的,我是在观察它。
他们说的东北人,一方面说的是深入人心的那些小品里的人。还有一方面,东北是挺复杂的,你是在厂区长大的,厂区它实际上在东北是一个被划出来的地方。如果是一个央企的话,它还会说我们是哪个中央部委下属的工厂,厂区里面的人口音都会很轻。
而那些像咱们说的典型气质的东北人,善于和人自来熟的、边界感不太强的东北人,它往往是在一些县城里生活的人,他们才是真正地方上的人,这个人群确实是有这样的气质,一上来男的叫大哥,女的叫大姐。这样的人首先我以我个人名义担保,在东北不是大多数。你认为东北人都这样,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声音大,他们搞出来的动静大,就像我们住酒店,在这一条长廊上有10个房间,只有1个房间特别闹人,声音特别大,你会认为只有那一个房间里有人,是一样的道理。
至于这种很典型的东北人的气质是怎么形成的,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参考。就是早期的东北人都是孤身一个人来到这里的,我们在这没有一个复杂的家族关系做背景,你所有的关系都需要自己建立,要硬着头皮去从0开始,那种情况下真的是谁的声音大,谁比较社牛,谁特别能够测试别人的容忍底线,谁就能够多拿到一些利益。这个往往是移民群体里面的常见状况。
大家伙会认为这好像是东北的地域特征,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里没有建立规则之前的一个常见现象,只不过是被一些人给放大了,把它变成了一种性格,甚至有人会认为这是一种美德。比方说有一些东北的酒鬼,他会强迫别人喝酒,会以他们那些酒场上的规则为荣,认为是一种文化,其实它还不是一种文化,我觉得这就是一套不怎么有价值的规则。
TOPYS:你观察,为什么现在大家都那么喜欢脱口秀?脱口秀的火爆,除了逗笑,还有什么原因?
贾行家:其实就是对人的兴趣。我们这次采访的是上海的这些脱口秀演员,他们喜欢用“脱口秀”这个词,但是在北京,很多演员他们愿意用“单口喜剧”的说法。
你怎么翻译stand-up comedy这个词,其实代表对这个词的两种观念、两种理解,但是这事说实话对我们来说不重要,甚至你这个东西好笑不好笑,我觉得都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你用一种什么样的情绪,用一种什么视角去观察世界和讲述自己。
有些演员已经有专场了,你愿意用一个小时给我讲一个事情,我愿意好好听一听你怎么看现在的社会,这就是我对脱口秀感兴趣的点。

TOPYS:这次接触了这么多东北籍的喜剧演员,有没有发现他们身上有什么共性?或者有什么区别于其他地区喜剧演员的特质或风格?
贾行家:典型的东北喜剧人的话会有一个很强的自嘲精神,他自嘲起来是很用力的,会把自己先贬损到相当强的一个地步,来在自己身上找包袱。他是敢于伤害自己、拆解自己的,然后他们会不同程度地把这个视角用到对象身上。
有一个小细节是呼兰观察出来的。呼兰说东北人和别人说话,他就不好好说,总要用一种冒犯对方的方式去说。他以自己的父母举例,老年人有一个习惯,就是一个东西买完了舍不得吃,快放坏了才吃,他妈妈就有这个习惯,他爸就埋怨他妈,别的地方的人会正向思维地说“那东西你不赶紧吃就坏了”,但是他爸是说“这你能吃吗?你不把它放坏了你能吃吗?”他就一定要用一种反问的方式。
再比如说老师找家长,正常情况下会批评家长“你不关心孩子的学习”“有问题没有及时跟我反馈”等等。但是典型的东北班主任,他见家长第一句话会说“最近挺忙的是吧?”就这么一句话,其实是在往你身上的痛点去戳。
他也没有恶意,但是他戳的过程,旁人看还挺好笑的。你也不知道他是寻求冒犯还是寻求搞笑,反正这是东北人的一个特征。
再有一个特点是我们好像还挺喜欢用简洁的东西来做喜剧的。我们搞笑的节奏很快,效率会很高。比方说如果是传统相声,他讲三翻四抖,其实它是会把一件事情的一个逻辑重复几次,直到你发现其中的扭曲和不正常,你才笑。但东北人是很直接的,赵本山就是这方面的高手,它不是通过一个节奏或者一个反常的现象让你笑,而是这一句话就让你笑。
谐音梗在东北特别多,比如有一个小品,高秀敏演的那个人物做梦梦见自己发财了,醒了之后要买金戒指,范伟演的角色就去劝赵本山(演的角色)说“你给嫂子买吧,嫂子现在也是个富婆了”,赵本山就说“什么富婆,她过去就是个泼妇”,这也算是一个谐音梗,它就是一个双关反用。这就是典型的我们东北人的幽默方式,这些东西的组合可能就会形成所谓的东北的喜剧风格。

#东北的魔幻和文艺复兴
TOPYS:你怎么看待由双雪涛、班宇、郑执这样一批东北80后小说家带动的“东北文艺复兴”?
贾行家:我觉得“东北文艺复兴”也是一个标签,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大家赋予这么一个标签的时候没有恶意,只是因为他要帮助自己用比较少的成本去理解问题。但事实上首先是东北的文艺过去究竟能不能叫兴旺的问题,然后才是它现在算不算是复兴的问题。
过去我们东北有那么多制片厂,现在都没人知道了,原来我们是有好多种文艺的。萧红那个时代,有一整个的东北文学,八九十年代,迟子健老师、洪峰老师、王阿城老师,这些作家都是很受全国读者关注的,所以文学这块可能一直也没有坏到哪去。
如果你真要去看的话,会发现东北现在也还有更多的好作家,比如长春的刘天昭、沈阳的苏方,每一位作家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个体,东北只是他们在一个时期的写作对象,但他们的故事是可以迁移的,主题都是各有特征的。我会觉得他们是哪的人,这事不重要。
比方说像双雪涛可能是最早受到关注的,他在《平原上的摩西》之后,开始正面地进入小说的母题形式探索,他的写作对象绝对不是地域性的,东北只不过是他用的一个符号一样的面相。他可能也会写工厂,写下岗,写东北的某一个时期,甚至写民国时代的沈阳,但是这些其实就像舞台布景一样,不重要。而郑执,从我的阅读经验来讲的话,他是一个朝向非常广大领域去写作的人,虽然他写《仙症》,写出马仙这些事情,但他用的是一个走遍世界之后往回看东北的视角,是一个俯瞰的视角。
班宇也是这样,班宇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文艺青年。他是在建立自己的一个世界,只不过恰巧在地域上和东北重合,很多人喜欢他作品里面的美。他除了天生是个讲故事的天才以外,他的东西还有一种美在。而这些东西都不一定是和这个地方血肉相连的,和上一代作家,比方说迟子建老师又不一样,迟子建老师和她的北极村的关系是不能割裂的。所以在我心目中,反而是这样的作家和东北的关系会更纯然一些。

TOPYS:书写东北一定不是从这几位作家开始的,为什么偏偏是这几位,在这个时候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把东北再次带入公众关注的领地?
贾行家:我的一个猜测是,可能和大家对于未来的某种预感有关系。如果一个人他觉得我生活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生活在一个可以去不断地追求更多财富的时代,他会去朝这个时代的前头看;但当他觉得自己处在一个倒车请注意的时代,后面有些事情要当心了,他当然就要往后看,看一看谁落在了后面,然后就看到了我们,是吧?就想问问我们有没有什么凋零的经验可以分享,我怀疑大家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观察我们东北人的。
TOPYS:受关注这件事,是不是也和东北地区的社会现象、文化现象的确有一种区别于主流文化的差异性有关?比如说这三位作家的作品中都多多少少呈现过我们东北地区的萨满文明,它就是极其不同于城市文化或者传统的儒释道文化所能产生的文明现象的。
贾行家:如果说大家真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话,会发现这种神秘学是全国各地都有的。有一些地方擅长的是符箓,而南方也有一些灵修、控术、巫蛊之类,它们都成体系,但它们的体系更复杂。我是喜欢这些东西的,我向来觉得多样性代表着安全,文化和生物界是一样的。
萨满现在也是人类学中的一门显学,而东北这一套,它的优点是它有一种生命力在,东北被开发的时间很短,所以我们相信的这一套东西可能里面保存的远古的成分更多。我们刚才说其他地方的原始巫术,因为对别的文化的引入和借鉴,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改造痕迹了。而东北这套东西很直接,说一个黄鼠狼也好,一个狐狸也好,它要控制你,和你的身体进行了一番搏斗,就像一个人训一匹马一样把你驯服了,然后你就成了他的“出马弟子”,它通过控制你去做一些事情或换取它要的东西,这其实就是特别简单的模型。
它的客观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庙,我们没有求神拜佛的那个空间,大家需要分散地解决问题。有一个老一辈的社会学家叫李慰祖,他说的一段话非常的有道理——你要相信这些农民是完全理解他的生活的,他不一定理解「什么是生命的意义」这种西方的问题,但是他对自己天天见到的是什么,生活中间什么东西管用,起了什么真实的变化的理解,以及他对农田、天气和这块土地的体验是远远比你城市人更深刻的。在这种基础之下,他相信这个东西有效,你不要认为那就是迷信。这种傲慢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TOPYS:有没有可能大家是在以拉美的魔幻主义为坐标,去理解东北的魔幻?也就是,当你的现实和你的传民间传说,还有你的历史,因为纠缠不清,没有办法把它梳理出来,所以会不自觉的把这一套东西混同在一起,好像形成一种文学上的气质。以《仙症》为例,一个人的苦难不光是因为具体环境的因素,也有时代的或者鬼神的因素,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东北一代人的命运,是不是可以算得上魔幻?
贾行家:如果我们用这个方视角去看魔幻的话,真的就有点无趣了。以拉美为对标,它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我们去看这几百年的拉美历史,他从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开始,就是几个文明在用不同的时速往一起撞。一方面这里有非洲人带来的巫毒文化,一方面是当地土著的阿兹特克文化,然后是欧洲人代表的技术文明、天主教文化,所有这些全都一下子对接到一起,还没有等到融合,像一杯鸡尾酒一样摆在这了,它确实显得挺魔幻的。
刚才我们说《仙症》,就是说神仙的世界、农民的世界和工人的生活,包括工厂倒闭之后的生活,没有经过一个平滑的处理过程,就被全部拼贴在一起了。大家都说“我的经验处理不了这么剧烈变化的一个现实”,就觉得这个事是一种魔幻体验,这个可能是有的。
但实际上可能也这一切并不魔幻,就是我们没细看,没把它分析出来。

#变形的和真实的东北
TOPYS:我们来借鉴一下木心老师刻画纽约的方法——如果让你用一两个你认为最有代表性的小故事来勾勒东北这块土地在你心目中的形象和气质,会是什么?
贾行家: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也不能算是个故事了,它可能没头没尾,但我能保证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
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小于子,我和他有数面之缘。可能是在我刚上大学那阵,通过一些爱好和他熟悉。他是个比我大几岁很腼腆的、大概就是从小县城来的一个朋友,大家在一起玩过几次。然后后来的一切就渐渐像孔乙己的故事一样,他的事我都是听别人给我转述的。有一段时间大家说小于子发财了,开工厂当老板了;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人跟我说小于子挺惨的,得病了,老婆死了;等到过了好多年,可能十几年之后,我才把这个事情拼凑完整。
小于子生活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煤矿城市。煤矿城市不只是有煤矿,它也有煤化工厂。这个工厂有一些说是国有的,但实际上它是承包给不同的地方企业,甚至会有一些外企,他们那个县城就有这么一个工厂。
有了这个工厂之后,村里的人就经常生病,最流行的是淋巴癌,好像还有肺癌,反正是流行的几种癌症,这个病在那里就像传染病一样,那些五颜六色、颜色鲜艳的水流到哪里,哪个村子的人就开始大面积地得这个病。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工厂就开始给大家赔款。基本的逻辑是你去查,你查出来这个病我就赔你多少钱,小于子的发财就是这么发的,先是他老婆得了这个病,然后是他自己得了这个病。
这个工厂看起来它不是个国企,因为赔款的金额还挺大的,赔了他们两个人将近200万,在九几年或者是千禧年前后。那个时候一般来讲,如果是一个煤矿工人,死于矿难,或者安全事故的话,也就是赔个几十万。
所以说一句混蛋的话,那个时候大家伙觉得得癌症也都值了——我就算是不喝这个水,我是不是也有可能得(病),那样的话,还没有人给我钱。
小于子和他老婆那个时候可能就是30出头的样子,得了这笔钱之后,这两个人没有着急治病。这很神奇,如果你看过阎连科那本《丁庄梦》,就会觉得小于子他们那些人就是书里描述的那么一个状态。
小于子当时用健康换了这一大笔钱,他就想投资,想自己做小老板。他有一个叔叔,开了一个砖窑,就忽悠他入股。那个时候,县里头弄一块地,然后在那地方砌几个烧砖的那种、像岩洞一样的建筑,就成了一个砖窑。这种私人的小企业可能会有一系列说服人入股的话术,比方他说城里正在盖楼,搞城市规模扩建,做这个有钱赚,并且说“你看你亲叔能忽悠你吗?你就把钱给我就行了”,我猜大概是这样。
这个砖窑后来当然就赔了,他好不容易从他叔叔破产的砖窑里拿回来了十几万块钱,这个时候时代已经进入到跟我们现在的感觉挺像的这个时代了。小于子岁数也挺大的了,他老婆已经死掉了,他自己这个病也是断断续续,他跑到他们县上面的地级市,开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是我听到的唯一一个开这种东西的人。它究竟是不是一个行业我不知道,我猜你也一定不知道,它叫做鞭馆儿。
就是会有一些人喜欢甩鞭子,他不是抽嘎,他就是在傍晚或者是凌晨的时候,用那种捆好的、大概两米多长、类似于新加坡的那种刑具式的鞭子,他拿这个凌空去甩,那个啪啪的响声作为他锻炼也好、发泄也好的一个过程。你要没见过这种缺德爱好的话,都很难描述有这么一种群众运动,那个画面就是周围的人也无法近他的身,你就看到一个人,像抽风一样,去甩鞭子。
小于子开这个鞭馆儿呢,是因为他发现了一个“商机”。东北冷,他觉得这些人到了冬天在外面甩怪冻的,他就自己租了个地下室,让这些人到地下室里来甩,他提供这些鞭子,搞了一个像是抽鞭子俱乐部,这么一个东西。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感受,我听到这个创业项目的时候觉得莫名的凄凉,能够感觉到吗?钓鱼还有一种悠闲在,抽鞭子就已经是一个按我们今天的话讲, loser到不能再loser的一个行当了,我看到抽鞭子的人,我都舍不得指责他扰民,因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扰民这个词,他好像被所有人欺负一圈,最后赶到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爱好里来的。
小于子这个故事在我这的结尾就是他是一个肿瘤患者,他在一个地下室里面收容了这么一群人在抽鞭子,这就是我听到的他最后的一个身影。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人最适合代表我印象中的这块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