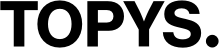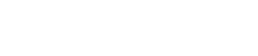二十年后,庆山在写些什么? | TOPYS专访作家庆山

大概十六七年前,我曾有一位好友,喜欢文学,热爱阅读。她和我说最近很痴迷一位作家的书,但她并不推荐我读 —— “太抑郁了,读起来让人沉重。” 我瞥了一眼封面,安妮宝贝。
但最近当我将庆山(安妮宝贝于2014年起使用的笔名)的新书《一切境》出版的消息告诉她时,她先是好奇地问: “庆山是谁?”,得到回复之后的下一句是:“她怎么还在写书?”
的确,和庆山同期的很多作家早已不再出版任何作品,投身去了其它领域,专心写作已经成为奢侈品。
在千禧年活跃的文艺青年们或多或少都翻过两页她的书,哪怕为了那短短的一篇“琼屑谈”专栏,《城市画报》也是不少人每期必买的刊物。
但也必须承认:并非每个人都会欣赏安妮宝贝的文字。有人觉得她笔触细腻,文风独特,能把握当下都市男女之间最敏锐的心绪,在每个无眠的夜晚捧起来总能找到久违的平静;也有人觉得她的文字矫揉造作,无病呻吟,似乎将最小的感受最大化,惹得众人一起不快。无论如何,安妮宝贝的文字以其浓郁的个人风格影响了一大批读者,甚至成为了一种“符号”。

庆山明白自己所受到的赞美与争议,但她还是选择藏在深深的幕帘之后,以一种“知我罪我,一任诸君”的态度面对外界的一切。这次借着《一切境》出版的机会,我们和庆山聊了聊。
1.去解决疑惑,而非陈述痛苦
“提到安妮宝贝(庆山),你会想到什么?”

我脑海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是“清净”。这样的印象来源于两处:第一她早期小说作品当中的人物形象往往是以一种“清醒而洁净”的面目出现;第二则是她在早期散文作品中所呈现的对于行走、城市生活以及个人情感的观察与思考,带给了读者一种安定且沉稳的阅读体验,犹如在草原驰骋,一马平川。
在阅读庆山的新书《一切境》时,并没有与往日的感受重逢,反而觉得“吃力”。密集却散漫的思绪记录让读者很难获得一气呵成的感受,不断地思考作者尝试表达的内容,就像是与她一起攀登延绵却不高耸的山地,不艰难,却吃力 。
对庆山而言,这样的文风改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过程,是一个作者在求索时所经历的途径。
“我在用‘安妮宝贝’这个笔名时才二十多岁。” 回头来看,庆山觉得所谓的青春都带有残酷性,会产生很大的痛苦,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逐渐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与以往的经验都要发生脱离。” 这些痛苦融入日常的生活中,如同隐匿于一杯醇美鸡尾酒当中的苦精。当作者尝试去书写时,她会将那些充满着“挣扎与矛盾”的苦精提炼出来。“安妮宝贝时期的作品代表的是那个阶段、在建立独立性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对你在探索的各种命题产生质疑,你会想要去找到自己的答案。”
但随着阅历的增加,人看待事物的角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以前觉得天大的事儿,过后思量其实也不过尔尔。这样的变化并不代表着妥协,反而是一种事物观的平衡,在这个过程当中,她继续用文字来“解决自己的疑惑,而不是一直在陈述自己的痛苦。”
她将这些解惑的过程记录下来,整理成册,用庆山的名字分享给读者。
这样的变化,并不是每个读者都能轻易地接受。好在,庆山也能轻松看透这一点,“书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选择”,如果缘分到了或者尽了,也是应该的。

这样豁达的态度在新书《一切境》里更加明显,全书分为四章,篇幅长短各异,而不同的段落与章节之间也并无明显的联系,庆山将她从哲学、宗教以及心理学当中攫取到的信息和在日常时所产生的感悟一一记录下来,描绘出她的思考图景,解析她对物质与精神的观点,这种极为自我的创作方式,让这本书更像是一份私人学习笔记和日记。在排版时,将透露出季节变化的内容放在一起,这样的阅读线索并不明显,却十分巧妙,让读者隐约跟随庆山走过一年四季,读罢心中盛满了对生活的思考与感悟。

从让人致郁的“安妮宝贝”到让人治愈的“庆山”,她写作的出发点与终点其实并没变,只是转换了看待事物的角度。“你不会总是困在困局里头了,总是会找到一些途径,你会找到一些自己的答案。”就像“当种子落下之后,我们只需要静静地等花开”就好。
2.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内容
写作二十余年,庆山依旧在继续。
30岁之前的她,不只是在“榕树下”时不时发表小说的安妮宝贝,也曾像我们一样,在金融银行、杂志出版、互联网、广告等行业就职。那时的她在商业区的高级写字楼上班,每日打卡,时常加班。“有时候加班到凌晨两三点,那个时候也很年轻,二十几岁,又处于互联网公司的高速发展期,有很多新的内容值得年轻人去加入创造。”她说:“当时选择的这些职业是因为它们都是有创意性的工作,这和之前银行的工作完全不同。”

虽然这些经历对她而言,并不像是一种值得托赖终生的“职业”,更像是一份求得温饱的“工作”,但她依旧兢兢业业地工作,“因为我本身是个写作者,不管怎么样也是需要去体验生活的。”
她从始至终唯一的“工作”似乎只有写作,写作对于她而言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发生,是探索生命的罗盘。
尝试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问答、专栏等不同创作形式,庆山的文风依旧具有个人特色,虽常有人效仿,却难以得到读者的肯定。这其实再正常不过了,在改用庆山这个笔名之初,曾有不少人好奇她为什么会脱下“安妮宝贝”这个掷地有声的笔名(或者用更商业化的词来形容:一个极具市场号召力的IP)?在庆山看来,笔名不过是一个代号,代表她在创作时所经历的不同阶段,而具体想要表达的内核却不曾有大的改变,这是创作者专属的特质烙印。“一个作家在表达的深度和广度会有拓展,但他/她个人的内核是不会有变化的”。

属于庆山的内核是人的内心。人们的精神世界始终是牵扯她写作道路的一条暗河,她溯流而上,追寻精神的源头。即便有人在感叹,昔日安妮宝贝笔下的“伊势丹与G-Star”化成了现在的庆山笔下的“坛城与海水”,但庆山的创作内核并没有太多变化,依旧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如果轻易能被改变,只能说明创作者的自我里没有一个坚定的意志力”。只是当创作者身处的环境发生变化,她通往创作内核的路径也随之改变而已,最终的目的地始终如一。
对于写作,庆山并没有深奥的方法论,她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天赋的能力,“如果你是适合写作的人,一大段一大段的句子会从脑海里蹦出来,然后再花时间去修改它们,完善它们”。但成为一名好的作家,所需要的却并不只有天赋。“作家能够去写作的时间是有限的,写作需要体力和脑力等综合力量来支撑,而这些力量并非无穷无尽”。从这个角度而言,成为一名作家真的是一份“出名要趁早”的工作。

“成为一名好的写作者需要敏感、真诚和有同理心”,敏感地捕捉身边的素材或者心中的思考,真诚地相信与传递自身的信念,用写作来与读者的同理心发生共鸣,在这些特质的加持下,各种修辞或叙事技巧已不再重要,就像武侠小说当中的绝世武功一样,“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大巧不工”,每一段文字重要的是“背后的内容”,是那些躲在纸张之下的力量。当然,作为一个主观创作行为,有时作者通过写作所传达出的内容会引来争议,庆山认为这些都仅仅是她的“一家之言”与“性情之谈”,并非绝对的结论。
3.孤独与对话,都是学习写作的方式
写作是一条孤独的路,一边是学习吸收外界的信息,一边是写作输出自身的理念,而连接这两端的就是作者自身,这对写作者是一个考验,“在写作时,你必须要让你的心神沉入到一个非常孤独的境地,才能写出比较深刻的内容”。

庆山在创作时,这条路的两端是家与咖啡店,在咖啡因和尼古丁的催化下,她将自己想要表达的一切录入文档。而在不创作的时候,为了保持生活的轻简,庆山并没有太多应酬与交际。散步、种花、喝茶并做大量而仔细的阅读,偶尔看场电影,与两三友人见见面。“如果没有疫情,我会在外生活,去远方常住,也许是大理,也许是拉萨。” 听起来过的是一种离群索居、与世无争的“神仙日子”。单调吗?不,当写作者找到了值得追随的主题之后,即便独身而行,也不会觉得孤单寂寞。也许是与外界的喧闹可以保持了距离,庆山才有空间能够静静地看花开花谢与云卷云舒,检视内心的变化和探索精神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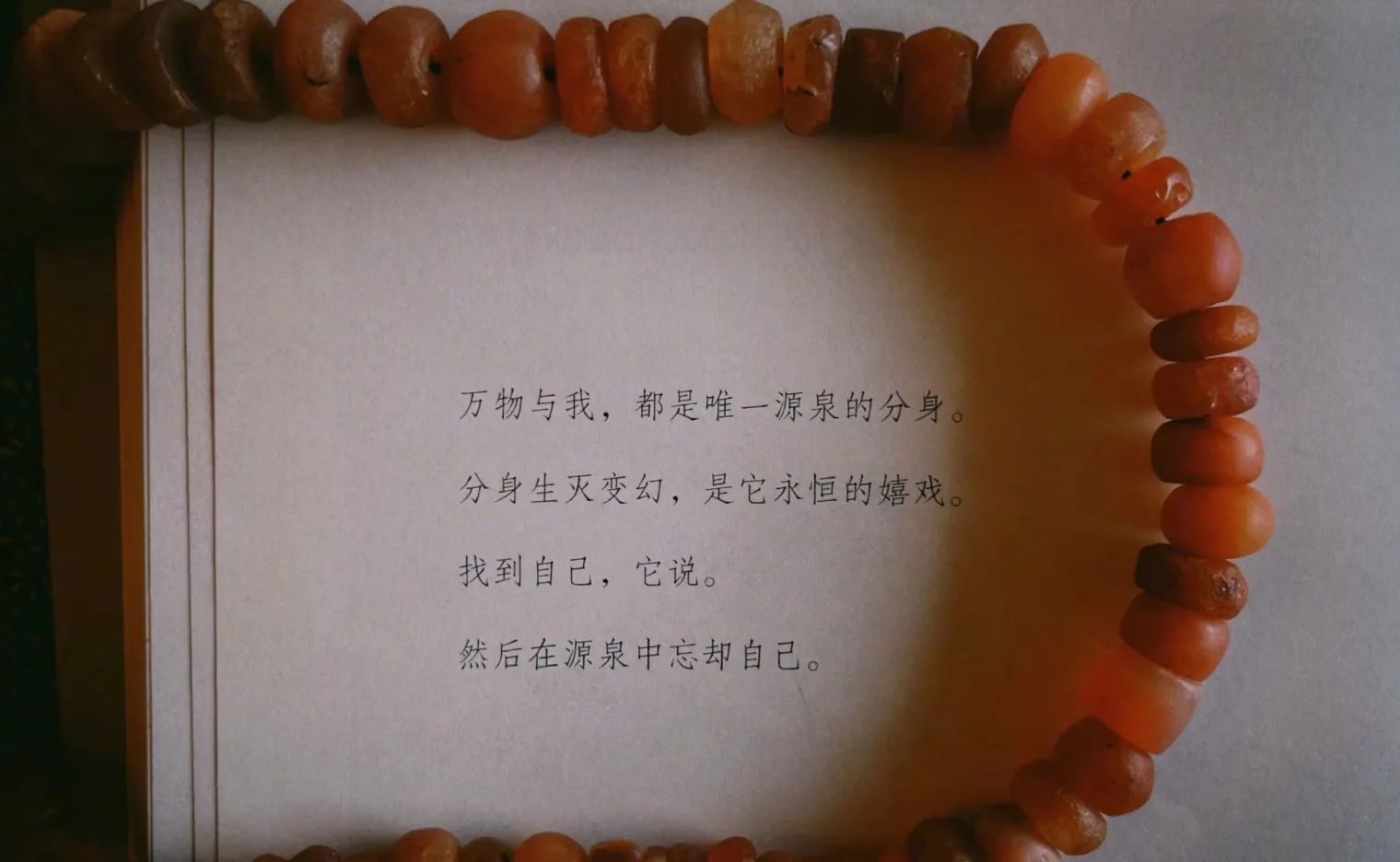
写作纵然孤独,但庆山却也收获良多。在她现在的生活当中,“信念”、“爱”和“自立利他”成为了最重要的三样事物。庆山的微博里总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私信,向她咨询情感、生活的大小事宜,庆山在仔细阅读来信人的困惑之后,会给予建议,她依旧认为自己从读者那得到的太多,而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写作者离不开读者,他们在通过写作给予读者的能量的同时,也从读者的反馈里收获到能量,“写作一定是被一些需要你的读者所推动和延续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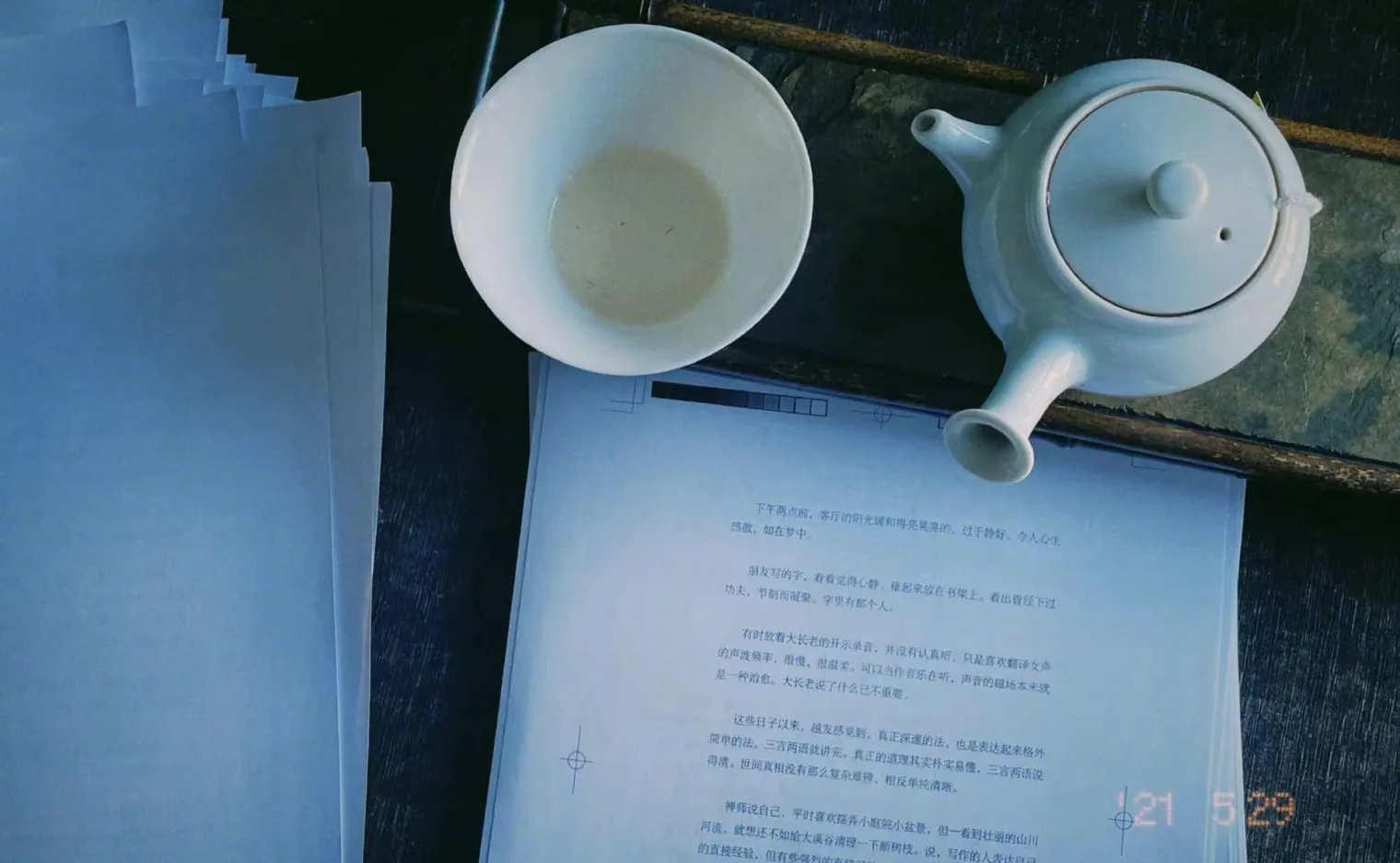
在近期的作品中,她常常会谈起“精神”、“生命”和“心灵”这些“大词汇”,好像只有“诗和远方”,全无“眼前的苟且”,即便只是将自己的感悟记录下来,还得落一个“何不食肉糜”的冤枉。
对庆山而言,对于内在世界的好奇不可避免,每个人在生命的阶段都会有种觉醒和深入的过程,而在这个阶段里,人会产生提升自我认知冲动,这是认识生命本源的一个过程,与宗教信仰无关。而在现在的社会中,一些人在不了解某件事物的前提下,很容易会陷入刻板印象的泥淖中,用“贴标签”的形式来认识事物,而这样的认知,其实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就像有些人认为香车宝马,华衣锦食可以是成功的象征,内心平静、喜悦祥和当然也可以是圆满的目标。
无论外界的声音有多大,庆山已经学会在这种喧闹的情境下用完成对生活的精神探索,我们依然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庆山对于生活思考的温柔缱绻,一杯浓厚的红茶,入口时会觉得艰涩,但等回甘上头,却别有一番滋味。
后记:
声音和我想象得差不多,多少带有一点江浙一带特有的温柔与安静。长达两个多小时的电话采访结束之后,她的声音依旧在耳旁回荡。

记得最开始读庆山的书是从散文开始入手,后来是看小说。我跟着她的笔迹路过香港、上海、西贡、墨脱和大理,见过都市的繁华,看到了霓虹灯之下的孤独与寂寥;触摸到大山大河的轮廓,走上通往秘境的崎岖山路。
不止是空间上的认知,因为她的作品,开始听杰奎琳·杜普蕾的大提琴,去看《她比烟花更寂寞》,开始觉得留婴儿般短发的女孩子很有魅力,开始向往活得肆意妄为的潇洒。现在回头看当时的一些想法,在觉得可笑幼稚之余,却又觉得理所应当 —— 这的确是属于那时的思维。
她从“安妮宝贝”变成了“庆山”,读者也在逐渐长大,很明显地感觉到庆山的文字更有力量,也更坚定,更适合现代人在忙碌时随手翻动,获得一刹的哲思火花或者一时的心灵小憩,探索内心无垠的宇宙。
真好,她依然在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