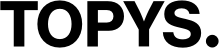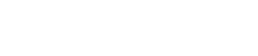山本耀司:GOD’S CREATURES 偶然之力
成功对山本耀司而言是偶然的,它甚至没有为他带来多少财富。在年近古稀之时回顾过去的30年,这位向来与社会意见相左的设计师表示,他只是“尽量身无长物”地在生活,季复一季地重复着他的“赌徒的生涯”,耐心等待着“神启般的狂喜”再次降临在他的伸展台上。

年近古稀的山本耀司依然像30年前那样说话行事。摄影/ 孙涛
从黑色合身长外套的袖口露出那一截半新不旧的白色罗纹袖口,让人还没看到脸,就知道坐在面前的是个上了年纪的人。山本耀司穿着一身家常衣服来到北京:简单的黑色单排扣风衣,白色衬衫,一条膝盖内侧已经起球的深藏青色针织羊毛裤,一双结实的深棕色户外短靴。“我一般都是两套衣服穿半年。”他说,“这是其中一套。”顿了一顿,他又欠欠身补充说:“让我解释一下,内衣我每天都在换的,而且我会穿Calvin Klein。”还没等人笑出来,他自己就先调皮地把手指放在了嘟起的嘴唇上。
山本先生常常在说话时伸出双手,从鬓边分别往后理一理头发。他的长发已经灰白,眼角往下耷拉,大部分时间看上去像是双目低垂,无精打采。然而他一个问题也不会听漏。“如果不做设计师,我会选择什么职业?我想⋯⋯画家?罪犯?”他漫不经心地抛出答案,“在这个世界上,说句实话,我是十分不幸的。我是战争寡妇的儿子,从小家里很穷,所以我始终不能很好地融入这世界。尤其在小时候,我总有一种反抗的劲头。如果没有通过事业来获得成功的话,我想也只能靠犯罪来排遣了。”
反抗——这是一种不常在老年人身上见到的气质。一个月以前,在Yohji Yamamoto 2012/2013秋冬发布会的后台,一群年轻的记者闯进化妆室向山本先生发问。“‘他们用英语问我:‘你今年多大了?’我回答说:‘我38 岁来到巴黎,到现在为止已经过去了30年。你算算,我多大了?’”他这样转述当时的情景。他并不掩饰回忆为自己所带来的乐趣。他清晰地讲起1981年刚到巴黎时,《女装日报》在他和川久保玲的发布会照片上打上的大叉,回忆起1985 年在美国接受记者访问,对方直截了当表达的羞辱。他回忆早年在东京的公司里,营销部门墙上那张日本地图是如何用红色图钉从函馆到冲绳标满了他的店铺位置,回忆后来在巴黎,尽管媒体一片恶评,买手还是蜂拥来到,挤坏了工作室的小电梯。他甚至回忆了一些不堪回首的事情:“好多人批评我,可是到了最后,我竟然获得了勋章(注:法兰西共和国艺术勋章,1994 年),开始有人把我称作大师,于是我突然不知道该做什么了。我开始从事音乐工作,还做了些现在不愿意去回想的事情。”这一次,他没有接着说下去,而是欣然收住话茬,享受听众那费解的沉默。
坐在化妆间里回答些诸如“今年贵庚”的问题,肯定比不上早年面对一群气势汹汹的记者来得有意思。不过对山本先生而言,这都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余兴节目。人生的高潮只有短短一瞬,它们出现在伸展台上。“一场发布会,通过录像来看,氛围不及现场的1/10。”他说,“观众一旦感受到了我的想法,就会热烈鼓掌——这种感觉对我而言就像毒品一样。事实上,这也是激励我从事设计工作整整30 年的源泉。”模特身着轻薄有如月光的长裙走上伸展台,却突然停下脚步,从裙子的拉链口袋里一口气掏出了鞋子、手套和捧花——重看这段1999年春夏的发布会视频,设计师本人还是难掩雀跃。他确实有过一些美妙时光。
对于一个在任何场合都承认自己“非常懒惰”的人而言,如果没有这种容易上瘾的刺激,恐怕一切就会不同。“为什么从事设计工作?我问我自己。”他说,“我懒极了。如果从事纯艺术,没有一个固定的发布时间,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开始。但时装发布就像作业,需要按时交卷。过去的30 年中,我一直在做着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与我的性格非常合拍。”他点上一支日本烟,可能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神来回答问题。只消聊上十分钟,你就会发现他任何问题都愿意回答,什么话都说。他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不时也会搞砸。“有时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直到做发布的时候还是不知道,到做完了还是不知道,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做完了。”与其说这是老年人看穿一切的轻松,到不如说更像年轻人毫无负担的冲劲。
38岁,山本耀司在东京对他的品牌老总,同时也是好朋友说:我想去巴黎。对方回答:那我们可没法跟你一起去。他说:我自己先去。从那时直到现在,正如他常说的,“30 年过去了”,他所追求的东西分毫未变。他坚持成衣比高级定制更有难度,所以他更喜欢做成衣。“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把服装放到店里销售,这有点近似赌博——如果有两季卖不出去,店铺就面临着倒闭,所以这是个冒险的行业。我战战兢兢地开展生意,一直做到现在。我对此很有自豪感。”眼前这位双目微垂的大师,在本质上是个劫后余生的赌徒。他从赌桌上下来抽支烟,歇口气,一会儿就回去。无论何时,只要说起当年大胜庄家的经历,他总不禁面露微笑,仿佛又一次触到堆积成山的筹码,嗅到空气里那令他上瘾的香气。
2009年10月,巴黎时装周刚刚结束,山本耀司似乎也要被迫离开牌桌。公司负债60亿日元,正式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对一个赌徒而言,这多少也是可以预料的事情,但并非游戏的终结。事实上,这位设计师所追求的,只不过是持续赢些小钱,让他始终有本钱在场子里待下去,继续享受上天不时给予眷顾的狂喜。他称之为“令人愉快的销售额”——在过去一季中卖出一部分东西,使之足以维持下一季的运营。“有人对我说:你并没有赚到多少钱,可见也不怎么成功嘛。但我认为赚钱并不是我想要的成功。我更在乎的是能否在作品中表达我想说的话,如果办不到,就麻烦了。”他说。他一点也不羡慕自己的同行朋友们,例如GiorgioArmani那奢侈的生活。“尽量地身无长物——这是我一直以来遵循的人生信条。”他说,“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担心,所有人都无法避免这一点。对我而言,只要能保证最低限度的生活就足够了。”
一点没错,说到退休之后的打算,山本先生的头一个念头,就是整天游手好闲地待在弹子房里。在年近古稀之时,他内心深处所需要的依然只是一间学生宿舍。“里面摆张床,让我在床上能做所有的事——工作、看电视、吃饭喝水⋯⋯感到厌烦的话,只要手头有个旅行袋,用一天时间就能搬走。”来到这个世界,生在东京,身为一个战争寡妇的儿子——这一切都不是山本耀司自己决定的,因此在他看来,生命从一开始便不公平。而既然被迫地获得了生命,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赌赌小钱,打发时间,等待那不知何时又会降临的人生高潮。“在创作当中,偶尔会做出超乎你想象的,让自己看了也感动的东西。有时在后台,模特换衣服的间隙,我会像观众第一次看到作品一样感到吃惊——这个东西就像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对此感到很兴奋,恨不得给自己打上200分。我觉得这是上帝给予的东西,不是自己做出来的。”他这样描述那了不起的一刻,“一个人要有能等待这种偶然的力量,我称之为‘偶然之力’。”
至于剩下的时间,吃吃最喜欢的米饭加日式腌菜,打打弹子,幻想着什么时候可以在家里吃老婆的软饭——其实也很不错。
就连成功,也是强加给山本耀司的东西。“这是买手们做出的决定,是偶然的。”他说。作为艺术家,他唯一的自觉,是“对大家公认美的、好的东西提出异议,不断地对现实产生疑问,并在此基础上创作”。“我认为,以叛逆的姿态为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他说。众所周知,这种叛逆的心态,也展现在他的审美中,例如对女性身体曲线的隐藏,又例如他对于服装背面更甚于正面的重视。“我的设计非常重视背影,这与我的境遇有关。母亲一个人把我带大,家里很穷,但我受到了强烈的爱——对此我很感激,然而内心深处,却并存着复杂的爱和恨。我对家庭主妇不感兴趣,只对在工作的女性有兴趣,而且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稍纵即逝的背影。一个女人从我面前走来,我无法正视她,看着她的背面,我反而想要叫住她。所以,你不觉得这些女模特的背影非常漂亮吗?你看不看得出来都无所谓,我也只是随便问问。”他说。
这类话题,只是在打弹子的间歇,走到弹子房后头夹弄里抽烟时跟人闲聊的内容。儿时经历、少年理想、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将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烟雾缭绕当中,自己说过就算,不用问听者感不感兴趣,明不明白。这只是在隐约传来的弹子机弹簧声里,享受着一片喧闹的寂静、充盈的虚空。

Yohji Yamamoto2012/2013 秋冬系列

Yohji Yamamoto 1994-1995 秋冬系列

Yohji Yamamoto 1999 春夏系列

1981 年,38 岁的山本耀司第一次在巴黎的伸展台上登场谢幕

Yohji Yamamoto 1981-82秋冬系列
B=《外滩画报》
YY= 山本耀司
不喜欢被称作日本人的日本人
B:你曾说过你不喜欢被称作日本设计师,这是为什么?
YY:一直到最近几年,他们在提到我的时候,还总叫我“那个日本设计师(the Japanese designer)。叫我山本也行,叫耀司也行啊,但他们不。不过,近来好像不那么叫了。1981年,我想在巴黎开个小店。在准备开业典礼时,有个女记者来采访我,提到另外还有个日本设计师也正在做时装发布,外界传得沸沸扬扬,说是“一群日本人来了”。我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有两个人,就被认为是一群人了。当时《女装日报》把我的设计跟川久保玲的拼在一起,在上面画了一个大叉,用日语写上“再见”,摆明了是说“我们不要你们的设计”。但我并没有为此觉得不快,反而很高兴,因为我获得了那么强烈的反应。大概在1985年左右,曾经有个美国记者跟我约了个特别采访,却当面骂了我一顿。他对我说:美国人不愿意开日本人造的车,更别提穿日本人做的衣服了。这不就是叫我滚出去的意思吗?还有个女记者,穿着红色的连衣裙,脚蹬超高高跟鞋,她对我说:我理解你。我回答:我不需要你的理解。所谓的理解,是高高在上的,意思是“我脑子里明白,但心里不接受”。我不需要这个。
B:既然如此,当初是什么让你决定把自己的设计带到巴黎?
YY:在巴黎做发布的时候,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我出生在东京,与其说是日本人,其实我一直更确切地觉得自己是东京人。念大学的时候,我从俄罗斯开始,到欧洲各地旅行。欧洲的那些国家,比如瑞士之类,我其实都不那么喜欢——可能是因为太干净整洁了吧。我穿过德国,到达巴黎。在巴黎的车站上,抽烟的人们指尖烟雾缭绕,车站上各种人的讲话声甚至叫喊声、灰尘的飞扬、各种气味的交杂⋯⋯让我感觉到这才是真正的有人类生存的地方。在这个瞬间,我被巴黎魅惑了。现在想起来,也许那个瞬间就是所谓命运的瞬间吧。所以,我甚至觉得自己是巴黎人。在法文里,有个词叫做命运的女人,日文中称为“魔性的女人”,意思就是一个决定了男人余生的女人——不论是好或者坏。对我来说,巴黎就是这个命运的女人。
B:那么在你自己看来,你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与日本美学有关?
YY: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问题。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日本人,我无论做什么,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都会从中发现日本元素。我其实并没有刻意地去制作有日本元素的作品。我自己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里沉睡着哪些日本的东西。
刚到巴黎那会儿,我特别觉得从日本来的设计师如果用和服元素去做发布的话,是一件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就像在卖旅游产品。到了巴黎之后又过了15 年,我觉得可以解开这个禁忌了,所以我提出一个与自己的本来观念相悖的目标,以和服为主题,做了一个春夏系列。
B:如果让你来开课讲述日本美学的精髓,你会怎么说?
YY:我在制作作品的时候,喜欢的制作方法,就是不百分之百地完成那个作品,怎么说呢,就是说会留下一些未完成的部分,不把整个作品做满。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 の美学( 留白的美学 )”一致的。我十分喜欢这个概念。
B:那么,你觉得你的设计与西方的美学有什么相通之处吗?
YY:西洋美学中,我觉得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是最让我接受的。比如说达·芬奇,我就非常喜欢。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有了一个老师带着多个学生,大家共同创作一个作品的方式。在那之前,艺术作品几乎都是由修道士等宗教相关人员来创作的,作品的背景也几乎都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古老故事。在文艺复兴开始之后,大家才开始用各种自由的想法来进行艺术创造,所创造的艺术品也能够让现代人理解。
不愿做设计师的设计师
B:看起来你的设计与整个西方的时装传统是两种东西。在西方的艺术家当中,有哪些人与你观念想通,因而成为了朋友?
YY: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说,世界级的艺术家被我喜欢的原因,很少是他的作品,而是那个人本身——他的生平、为人处事、价值观。与我成为挚友的两个艺术家,一个是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另一个是皮娜·鲍什现代舞蹈团的编舞师考利·阿古拉法。跟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即使不说任何言语,都觉得是可以互相认同和感知的,所以立刻就成了挚友。
我和文德斯的相识,是在巴黎国立美术馆。顺便说一句,巴黎国际美术馆是以钢筋等现代材料建成的,和巴黎的整个风貌可以说格格不入。那时候,这家美术馆向我发出了个展邀请,但由于我当时正是意气风发地工作着的最高峰时期,一心只想着往前,进行更多新的创作,一点都不想去回顾过去,因此一口回绝了。但对方表示,即使不是实物,胶片影像也可以,所以我就答应了。当时被介绍认识的合作艺术家,就是文德斯,在认识的瞬间,我们就感觉如同亲兄弟一般。
B:那些与你同样在西方享有盛名的日本设计师呢?川久保玲,三宅一生——你跟他们如今还有联系吗?
YY:我的态度是彼此尊敬,尽量别见面。
B:你说过你恨时尚。如果说设计不关乎潮流,你每次发布所要表述的理念又是基于什么?
YY:我一直反感被称作时装设计师。每次从巴黎回到东京成田机场,需要填写一张入境表格。在职业那一栏中,我很不想填上“时装设计师”这几个字,过去,我会用“法人代表”或“公司高管”来糊弄。我从来没有设计过流行的东西,相反,我是一个反流行,反时尚的人。我从没走过康庄大道,始终走在独木桥上,这也意味着我的作品销量不会很大。说到艺术家,他的作用是什么?我认为是对大家公认美的、好的东西提出异议。我坚信这一点,始终在这一前提下工作。以叛逆的姿态为社会作出贡献,这就是艺术家的使命。
B:你曾尝试在高级定制时装周期间发布成衣系列,为什么后来没有继续下去?
YY:以前的欧洲人都是在定制时装的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大家认定定制时装才是最高级和时髦的,而批量生产的成衣不够格调。那是在1990 年左右吧,我非常想向民众传达一个想法,就是批量成衣其实比定制时装更加高级,制作难度更高。因为批量成衣没有客户的订单,没有个人尺寸,但是仍然能够使穿着的人显得合体美观。定制时装要量尺寸,经过两到三次修正,整件衣服完成甚至需要3 个月以上。这完全不符合时代潮流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我个人完全认为,成衣的制作难度要高出定制无数。所以当时,我故意借高级定制时装周,搞怪地展出了自己的成衣。因为目的只是为了表明想法,所以一次就足够了。
没有雄心壮志的雄心壮志
B:这个问题相信你想过很多次,有一天退休之后,你将如何生活?
YY:我的理想状态用日文的老话说,就是想变成个纸老公,让我的发型师妻子赚钱养活我,这个就是我的梦想。我平时就钓个鱼,打个游戏,赌个小钱。
B:可以告诉我们你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吗?
YY:日本的白米饭。小菜的话,只要有腌菜就满足了。这次在中国吃到了海参,在日本是吃不到的。看起来怪不舒服,但确实挺好吃。
B:喜欢哪些艺术作品呢?
YY:其实我对于各个形式的音乐作品都很喜欢,但是最喜欢的是美国黑人所创造的蓝调音乐。至于文学作品,过去上学的时候没头没脑地阅读了不少俄国文学,最后念的,同时也最喜欢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B:到了现在这个年龄,你是否感到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与年轻时有所不同?
YY:基本上没有变化吧。不过,当我很直接地感觉到年龄增长时候,就觉得是有一件想要去做,但是完成不了的事情。这话题可能会变得复杂吧,简单地说,我觉得现在的文明进步有一些过头。怎么说呢?例如科学家,大家都是在努力研究,不停地发现和发明新事物。但是对于这些新事物会造成的后果,大家都没有考虑。比如说核能,地震后日本的核电站泄漏就是很好的例子。我觉得事物的进展应该在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影响的前提下进行,但是现在的整个人类社会已经是跨越限度地发展了,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过度发展的时代。要将这个进程停下来,拉回正常范围,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需要全世界方方面面的人的努力。假如说是为了这个目标的话,我会尽全力,说所有的话,做所有的事。

Yohji Yamamoto1984春夏系列

山本耀司在品牌2012/2013秋冬发布会后台
via 《外滩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