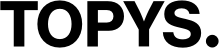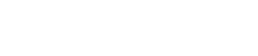六十年三地歌之8:都市忧郁(1989-1994)
1987、1988年的时候,在“西北风”的大嗓门之中,突然风靡起一种小嗓门。一群来历不明、国籍不明的女人,统统打着“东南亚红歌星”的旗号,唱着甜腻腻的中国小调,把“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之类的甜俗情歌,唱滥了城市和小镇的每一个街头。
最出名的“东南亚红歌星”当数龙飘飘、韩宝仪、谢采妘。1987年的某天,都市的唱片柜里出现了一张怪片,“快乐唱片”的商标下,“东南亚红歌星”谢采妘的甜媚圆脸后面,站着一个全身蓝衣的男子。这男子夹克无领,钮扣不扣,长裤上肥下瘦,皮带宽有四指;最奇怪的是发型,乍一看是平头,但前额开出小菊花状,后脑更有长长、泡泡的烫发直垂到肩膀。这怪片的名字是:《齐秦·谢采妘:燃烧爱情》。
除了两人合唱的《燃烧爱情》,磁带里通篇是齐秦的独唱。跟以前的“快乐唱片”全然不同,这磁带里的歌非常冷。这张中图版原装磁带标价十五元,相当于一个大学生十天的生活费。通常,十五元的原装带都不会太流行,因为太贵了。但是没多久,专辑里一首《大约在冬季》,成了1988年最流行的歌。
不只这首歌,齐秦上身的夹克、下身的裤子也流行了,那夹克叫立领夹克,那裤子叫萝卜裤。时髦青年也想学他那头型,但是不敢,只好学一半儿,把前额的头发烫成菊花状。
这一年年底,标价八元五角的引进版齐秦也发行了,名字叫《狼》。专辑一开头就唱:“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走在无垠的旷野中”。
齐秦带来的轰动是从来也不曾有过的,此前,通过磁带进来的港台歌手,从没有流行到这个程度,它不仅是歌,还是一种新锐的城市风尚,还传达出不可思议的新生活、新文化的气息,还带来一个你从来没见过、也从来不可能想象过的人格形象:狼的形象。
在足足有三年的时间里,青年人追逐着齐秦,费力地寻找着他的每一首没听过的歌,尤其是那些关于狼的系列歌曲。由于海峡两岸的阻隔,许多在台湾发行的歌,大陆还听不到,但是,完全是传奇性的,这些歌曲通过在青年中相互借听、拷贝,迅速成为半地下、半神秘的流行作品。
狼,人;旷野,城市。这样的两对形象,在齐秦的世界里变成了一个形象。城市如旷野,人孤独如被抛弃,抛弃到冷月下、长街中、水泥的丛林里,渴望着温暖,不知道方向,他发出了凄厉的长啸,但是回答他的,只有冷冷都市冰凉的回声。
在中国流行音乐中,这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创造。围绕着齐秦的自我设计,陈志远、游正彦、许治民、黄瑞丰、黄大军、陈升、周治平等一批音乐人协力创作,打造出一个人歌一体、人戏不分的狼的世界。
这狼有时乡愁:咬着冷冷的牙,报以两声长啸,不为别的,只为那传说中美丽的草原。
这狼有时《独行》:我在风里踽踽独行,我在夜里独自哭泣;独自走在这生命的荒原里,独自走在这无尽的期待里。
这狼在黑夜里《巡行》:午夜的都市,就像那月圆的丛林,我们在黑暗的街道巡行,怀抱着一种流浪的心情。
有着人的脆弱、狼的心情、时髦青年的酷,这些歌曲散发着天人合一的凄美。面对这样的歌,连听歌人也会困惑,那个面对着《冷月》的是青年还是孤狼?“抬起头仰望着黑夜,我的眼闪烁着凄迷,独自在黑夜哭泣,呼唤冷月。”而站在两峰交汇的《垭口》,这个人不知自己是谁,只听着北风嘶吼,不说话,因为他来自垭(哑)口。当北风不息、月落大地,他的心中滚落着这样的话:“他们说我原是一匹狼,曾在不安的岁月中迷失。唱一首歌叫做生命,却不知生命为何。”
人群中的孤立感,一如动物中的狼族亘古如一的寂寞。红尘中,独步的一匹狼,迢迢遥想着山林中壮阔的往事。这样的形象打动了大陆青年,在齐秦的许多歌曲还没有进来时,大陆歌手竞相仿冒他的新专辑。有一盘磁带,将关于狼的所有歌曲集中起来,号称齐秦最新专辑,不起眼的角落,却用最小的字号印着,“屠洪刚演唱”。
在差不多三年中,齐秦唱出了一只狼的各种形象:荒原中的狼,独行的狼,长啸的狼,哭泣的狼,冷月下的狼,垭口中的狼,蛰伏的狼,出没的狼、奔跑的狼……这种手法非常新颖,几位台湾音乐人以拟人和象征手法,把狼的生活习性、生存百态写了个遍。有一首在大陆小范围流传且非常难找的狼歌,叫做《出没》,这样唱:尘土飞扬越过大地,依稀可辨我的足迹。……生存在这轮回里,我是不需注解的谜,出没。这条路有一个方向,去向一个遥远的传说。传说中有一行足迹,是我唯一出没的痕迹。
此后,齐秦始终活跃在舞台上,差不多流行了二十年,一种个性风格如此长盛不衰,在华语歌坛极为罕见。即使在后期,齐秦不再打出狼的旗号,一些歌曲却依稀可见狼的神魂气度。如1998年的《追逐》,这样唱:“你和我之间,在传说中的天地徘徊,追逐的日子直到永远。”同一年的《边界》,反复着这样的句子:“就在前面不远的一个地方,越过了边界。越过生命最冷的一个冬天,一切从头。多少迷惘和灿烂的往事,在这边界也显得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齐秦的许多歌曲都暗暗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站在八十年代的末尾,前一个时代的光环,渐渐散去,齐秦面对的是旧生活旧理想崩溃的一代青年。这一代青年曾受着理想、世界观、光明的人类未来的教育,但随着“文革”(大陆)、“戒严时期”(台湾)的彻底结束,随着各种哲学思潮不断冲刷,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社会的理想是什么?这样的问题,突然变得那么难于回答。在突然而起的都市浪潮中,这一代青年迷惘、幻灭、失落、矛盾重重。狼的心情,就是无家可归的人类的心情。《九个太阳》歌词回望着那个太阳灼热的远古,说得如此明白:“在没有理想的土地上,住着一群陌生的人,不知道什么是笑,什么是眼泪。”伴随着齐秦的出现,凶猛的都市风吹过来了。
1989 年秋天,中央电视台不知出于何因,突然在两个晚上的黄金时间,连续播出两集《潮——来自台湾的歌》,它以MTV的形式,首次介绍了台湾在1988、1989年当红的流行歌曲。这真是一场视觉盛宴,大陆人第一次见识到了音乐电视,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视觉体验。
曾经,英国电子乐队“杜兰·杜兰”的音乐电视,一度震撼了导演陈凯歌,使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电影语言。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在西方成长了足有十年的新艺术,每个人的感受恐怕都是震惊,即使是像陈凯歌这样见多识广的电影专业人士。
台湾流行歌曲一下子变得如此生动,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之前,大陆人虽然一直惯用“港台歌曲”的称呼,却是香港歌占了多数,台湾除了邓丽君、刘文正,在人们头脑中就只有校园歌曲、日月潭、阿里山这样的陈旧概念。《潮》的播出,使大陆人窥见一片歌曲的新大陆。
童安格,时人称之“白马王子”。有着俊朗的外形,艺术的气质,雕琢而略带些自恋的嗓音。1988年以前,他是个喜欢来点小玩闹的大男孩,虽然大陆引进了他的专辑,但知道的人并不多。1989年,童安格新学会的狠劲儿,让他的创作和演唱突然地成熟大气起来,他就这么用那种又狠又深情又自恋的演唱,一举征服了海峡两岸的听众,让所有的城市都回荡起他的歌声。
童安格的情歌深情舒展,带着书卷气。他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遗憾唱得那么大气,像一辈子的憾事那么沉重,像心海的波涛无尽翻滚一般广阔。他唱《花瓣雨》,说“失去了你,只会在风中坠落”,还说,“你的谎言像颗泪水,晶莹夺目却叫人心碎”,这般歌词配上深情款款的旋律,真是让人心痛。
童安格不只写情歌。他还虚构了《耶利亚女郎》的传说,说“得到她的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他还在错误、恐惧、谴责、茫然、悔恨、教训中在忠孝东路徘徊,高唱“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漂流;让生命去等候,等候下一个伤口。”
这些歌曲雅俗共赏,又似有深意。
原版引进台湾流行歌曲的潮流,突然像开了闸,一批接着一批。即便这样,也依然赶不上狂热的听众要在第一时间听到台湾最新曲目的渴求。1988年开始的磁带拷贝生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骤然火爆。一些有海外关系的人,将在台湾流行的原版录音带通过各种渠道带入内地,用空白磁带复制数百份,拿到街头、大学校园里兜售,形成了台湾流行音乐在两岸同步流行的景观。
大城市的街头,磁带店如雨后春笋,闹市区几乎每隔一千米就有一家。一首首当红歌曲,一路走去不绝于耳。
这个时期特别盛产男歌手,男歌手一个比一个更受伤,相比较起来,童安格那种《忘不了》的心碎,就算是健康和明朗的了。
王杰的心痛和姜育恒的忧郁名噪一时。江念庭有一首歌,叫“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确实,听这个时期的台湾歌曲,感觉满大街都是寂寞的朋友。
从1987年到1994年,王杰大概出了十四张专辑。十四张专辑几乎张张只唱失恋的爱情。对这个痛不欲生、哭哭啼啼、痴情得一塌糊涂的男人,每出一张这样的新作,众多歌迷照样去捧场,那情景真可谓一“哭”百应。
王杰被封以“浪子”的雅号,他的歌总体上都凸显了一种失败,有一种“注定失败,永远失恋”的情结。他的成名作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紧接着以《忘了你,忘了我》、《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我要飞》等歌曲反复渲染。并不像这些歌名所暗示的,王杰从来不曾潇洒,对他来说,爱情既不会是一场游戏,更不会是一场梦;忘了你做不到,忘了我更是甭谈,我要飞那是永远也飞不起来的,他好像沉陷在痛苦的泥淖里,被悲剧般的心痛紧紧地拽住了双腿。
王杰有一首名作叫《为了爱,梦一生》,堪为他的写照:“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
与王杰相对应,被称为“忧郁王子”的姜育恒,则是另一种苦相。
姜育恒有首歌叫《一如往昔》:“一如往昔,天已微明。一如往昔,寂寞冷清。一如往昔,我没有你。有泪,有酒,有我自己。”
酒气弥漫了姜育恒的每一张专辑。他沙哑的喉咙像是被酒泡过,被烟熏过,被苦水腌过。因为失意而痛苦,这让他一再地沉湎于酒,只想一醉方休、长醉不醒;他是如此的伤感,似乎只有这样才足以忘掉苦痛的一切。
《驿动的心》表明姜育恒是在路上,他的歌曲足足有一个系列,表明他一直在路上。旅途,流浪,辗转流徙,这是姜育恒一再重复的主题。“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这样漂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在李子恒专为他写的《一个人》当中,这种“在路上”的情结终于上升到一辈子愁苦的高度:
一个人 度过了多少情缘/一个人 度不完魂梦一生/一个人 依旧是梦柯一生/一个人 是永远的渡梦河
姜育恒的嗓音沧桑沉郁,演唱中更有渲情至极的用力,直让人愁肠百结,暮气沉沉。《一世情缘》、《再回首》、《跟往事干杯》,这些歌经他演唱后,都成了名动一时的流行曲。
很多时候,台湾歌手唱的不外乎是情歌,因为只有情歌才能大众,才能最广泛地流行。但有意思的是,唱情歌竟也能卓示个性。
台湾男歌手唱的歌,几乎都是自己写的,都是自己性格和经历的某一面写照,这让这些男歌手不像是唱片公司制造出来的,而就像是他们自己。
这一个个个性,不再是经典艺术中差异明显的独特艺术风格或个人表达,而是在大众歌曲的统一面目下,展示歌手非常感性的方面。
庾澄庆以带有轻摇滚风格的《让我一次爱个够》、《改变所有的错》,在九十年代初占据了一席之地,唱片公司给他的宣传词是“霸气中深情无限,温柔中自信凛凛”。这个性真够感性的,不是什么艺术主张,也不是什么人生观念,但细细琢磨,你又不得不佩服它的贴切到位,无论用它描述那歌风,还是描述那歌手的长相、性格,都极为传神。
伍思凯又是一个类型,他是以台湾化的蓝调腔独树一帜的。他高亢的、在高音区有利刃感的声音,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终于让他大红。他的一些半流行的歌曲,品质更高,如“整个世界的寂寞,像个影子跟着我” (《整个世界的寂寞》),把他声音中的力度发挥到了极致,具有犀利的失落感。而“New York,Dallas,Los Angeles,寂寞公路每站都下雪”,“下雪街头独自地行走,握不住一杯温热的咖啡”(《寂寞公路》)的低吟,充满了一种世界大都市的极致伤感和浪漫。
1988至1994年,是台湾都市型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嗓音各异、个性独特的歌手,更奇特的是,这么多歌手几乎都处在创作的巅峰期,几乎每个人每年都能拿出一张佳作,因此毫不含糊地开启了整个华语圈的“台湾时代”。
周治平的嗓音不算独特,创作也不算偏门,依然是些风花雪月,但他唱这一主题时,却能写出“月光与星子,玫瑰花瓣和雨丝”这样的惊艳用词,而且,他有意地使用典故素材、古代女子故事,来抒发古今不变、千年不易的情衷。较诸一般情歌,《青梅竹马》、《苏三起解》、《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不落俗套,特别的古雅、清丽、婉转。借助着情歌,周治平还特别表现了“任凭时风变幻、我依然纯真如故”的端庄坚持姿态,这已不只是爱的抒情,而是人生态度。这样细密的心思未必能被大众体察,但一定会潜移默化。无独有偶,不满足于写情歌的张洪量,一面以《你知道我在等你吗》、《美丽的花蝴蝶》这样的情歌占据着流行歌的山头,一面“不按牌理出牌”地写出《爱与生的苦恼》、《逃亡》、《蜕变》、《失真》等略显严肃的主题,同时,他还以严谨的对位法,以建构中国式交响乐的雄心,在一首首小曲的后面,持续地谱写出俯视流行大众的格调高雅的古典主义配器。
郑智化是一个走路靠双拐的残疾青年,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刚出来时,郑智化比周治平和张洪量更走极端。他以明显显异出病态和虚弱的哑嗓,建造了完全属于个人的孤寂世界,这个世界灰暗封闭,充满绝望和宿命,好似一条展示着失败和虚无的人生画廊。《老幺的故事》、《卸了妆的女人》、《淡呀淡的光》、《堕落天使》,都是令人一见难忘的凄美人生画面。这样的歌当然不会太流行,但两三年后,郑智化突然心境陡转,写出了《年轻时代》、《生日快乐》、《水手》、《星星点灯》这样的歌,这些依然带着颓废底色的作品,却能让人从励志的角度,抓住昂扬向上的“光明的尾巴”。从此,那个绝望的郑智化,不仅被大众也被他自己,永远地忘记。
此时的流行音乐风景,众星云集,众星璀璨,好像在拥挤的时空中,每个人仍然可占据一大片的位置。如此情境中,脱颖而出其实是极为困难的,如果说这时候需要什么利器的话,那么,最利的利器就是嗓子,一个与众不同、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嗓子。
早几年,杨庆煌曾享受过嗓子的好处。在那个台湾风还没有刮过来的1987年,毫无名气的他竟以一根青涩嘹亮的直嗓子,把《菁菁校园》唱成了好似大陆每一所大学的校歌。
天赋异嗓的张雨生,最初听到他的人不一定都喜欢,但每一个人肯定都会吃惊。这样高的嗓子,像是少年,又像是女声。飞碟唱片用这种嗓子打造“和天一样高”的少年梦想。《我的未来不是梦》、《天天想你》、《大海》、《一天到晚游泳的鱼》相继走红。戴着黑框眼镜,永远长不大的少年,驾驭着超人式的高音,像乘云踏风的哪吒,一往无前追逐梦想。张雨生后来做了很多改变,但这样一个大众心目中的形象,竟像永远也擦不去。
台湾乐评人翁嘉铭曾经评论说,台湾的流行歌曲向来只重唱功,特别有对男高音的崇拜。确实,这个时期出现的男歌手,都能看出这种崇拜。张信哲是宛若唱诗班中男童的高音;优客李林是唱假声如同在摩天大楼间穿花的高音;文章是硬朗的、阳光的、霸道的高音;黄大炜是钢铁般厚重、人性悲叹般浩大的高音。不同于众多流行好嗓的纤细精致,黄大炜的歌声将它们统统击碎,李宗盛称赞它“将会令许多自以为会唱歌的男歌手虚心检讨。”
情歌的外表,宗教的深度。这是难于解说的。有时候一种声音,完全超出了它歌词的内容。黄大炜的歌声不仅表达了他自己,还往往能覆盖更为广阔的时间和人群。他的歌声不是个人的,而是人的;不是情绪,而是感情;不是伤心,而是悲恸;不是一次受伤,而是永远剧痛。总之,它具有一种形而上的、崇高的格调。用这样的声音内涵,黄大炜完成了两首杰作,1990年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和2000年的《秋天1944》。
高明骏和张镐哲都有风沙般的嗓子,高明骏甚至更激越,但是他就缺少崇高的格调,没有那种哲学味儿,顶多是一件异嗓,或者就是“来自缅甸的丛林男孩”那样的形象。张镐哲不同,他跟黄大炜一样,歌声中有整个人生的滋味。他唱《旋转门》,这都市中习见的场景,在他口中却变成了异样:“转进去能不能把从前忘记,转出来能不能让一切重来?我站在旋转门的面前,却怕看到里面的世界。”
世界,就是像这么大。张镐哲是个韩国人,他唱的歌,很多时候词虽然简单,但他那如同重伤风的嗓子,却把简单的词唱得像人生那样重,像时光那样沧桑。《再回到从前》、《北风》、《镜子·空瓶·三十年》,这些歌如果不是张镐哲唱,也就是一些伤感的歌曲罢了,但张镐哲唱了,它的内容和意味儿就全变了。
殷正洋、李恕权、钮大可、曲佑良、费翔、钟镇涛、邰正宵、姚可杰(“东方快车”主唱)、曹松章、张宇,前都市派的刘文正、费玉清、陈彼得、黄仲昆、高凌风,也都是些别致、极致的男嗓。
其实越是独特的嗓子,要广泛流行就越是不可能。那种各界通吃的歌喉,一定会是比较健康、温暖、深情、周正的。所以,这一个五年乃至十年,华语乐坛销量最大的男歌手,是台湾歌手周华健和唱国语的香港歌手张学友。格调与之类似但形象风度欠缺的巫启贤、郑中基,则获得了较短时期的成功。
虽然这个时期的大陆听众,有一种照单全收的兼容并包,但还是有些题材独具、内涵深厚、极其个性化的歌手,几乎完全被忽略。比如黄舒骏,虽然在台湾极为出名,但对于大陆,则要再等差不多两个五年,才在一定的听众范围内知名起来。
同一时期,台湾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女歌手。女歌手不及男歌手个性分明。女歌手往往不事创作,而是在著名制作人的导演下,唱出都市女子的心情感悟。
这些著名制作人中,李宗盛和小虫是最突出的。李宗盛本人是一个民谣歌手,在中文口白式唱腔及其旋律制造上有独特心得。他特别注重诚恳的歌唱态度,努力体会城市现实中真实的情感变故,擅长叙事体,口语化的词与曲浑然一体,并对歌手本人的个性潜质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录音时,李宗盛极端重视细节,对完美的要求近乎苛刻,这让他精准地为许多女歌手都制造出了质量上乘且流行畅销的作品。他的创作如同一部都市女性的情史大全,张艾嘉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
比起李宗盛,小虫似乎更感性。在音乐上,他喜欢在美国黑人节奏蓝调与中国曲风的调和上作文章。但他的制作之道,神奇的却不在这里,而在于他好像对女性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宠爱,他并不像李宗盛那样控制女歌手,而是与女歌手合作时似有暧昧的互感在微妙地发生作用,并最终散发出迷人的浪漫遐想。他是那种特别明显的与女歌手合作比与男歌手合作更成功的制作人。
几乎是男人在体会着女人,台湾的都市女性有了她们的代言人。陈淑桦、潘越云、蔡琴、张艾嘉、黄莺莺、杨林、邓妙华、王芷蕾、张清芳、林慧萍、曾庆瑜、于台烟、叶欢、千百惠、许景淳、赵咏华、李之勤、邝美云(香港)、孟庭苇、万芳、辛晓琪、李度,还没改名的王靖雯,变成了台湾媳妇的香港女子林忆莲,从大陆转往台湾发展的那英,从新加坡来的许美静,从马来西亚来的柯以敏……她们一路唱来,唱出都市女子的情路,个个称得上声音优质、感情细腻、词精曲美,但没有一个人,立得起一个完整的女性形象。
潘美辰差一点创出了另例。她以不柔和、显生硬的唱腔,中性的风度和个性,自写自弹自唱,塑造了冷酷的、“拒绝融化的冰”的形象,预示着下一个时期女歌手独立自主的风采。
同潘美辰类似,台湾女歌手中还颇有一些异嗓,娃娃、李丽芬、林良乐、黄小琥、李翊君、彭佳慧……她们声音比较粗粝,有时兼有男性的品质,难于归入都市女性的定位。女异声们各有绝色,歌坛上的一些奇品异品歌曲常出自其口。
曾经,大陆的创作者,甚至也包括大陆的听众,有过强烈鄙视港台流行音乐的时期,他们共同的感受是,港台歌曲肤浅、庸俗、没文化。但经过1989年之后的五年,已经没有人再说它没文化了,因为在都市情歌肤浅的表皮之下,竟有这么多复杂难言的内容。一首小小的情歌,有时也可能具有人生的重量。对歌曲的接受方式也变了,过去,歌手只是作曲家所写的某一首歌的表达者,现在,听一首歌,不只得到一首歌,还得到一个人,一个商业与歌手本人合谋的都市人格。
遥想1927年,上海作曲家黎锦晖创作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开篇之作《毛毛雨》。八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经历了“红色歌曲”、“战斗歌曲”为主体的三十年,传统曾经一度断裂,但在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地区,流行音乐从未中断过,这段台湾音乐风靡大陆的过程,实际上是音乐传统全面反哺回乡的过程。从台湾歌曲中,能听见唐宋诗词的中国美学,能听见中国人惯有的人生感怀,也能听见华人血脉中历经数百年仍在起起伏伏的诸多母题。即使是专业的创作者,这时也感到,流行音乐,这是一种可轻可重的音乐形态,这是悠久传统的脱胎与新生,这是一股无比强大的都市新文化,它汹涌而来,最终会将一切改变。
1994年,在忧郁的都市风吹过后,整个社会的音乐生活,遂转向了完全的都市生活形态。在一个更丰富、更商业也更娱乐的场景中,歌手亦俗亦雅、见歌见人的魔力逐渐褪去。下一个时期的人物,男歌手如游鸿明、李圣杰、萧煌奇、吴克群、卢广仲,女歌手如许茹芸、周蕙、徐若瑄、刘若英、江美琪、戴佩妮、孙燕姿、范玮琪,再也享受不到这个时期的美好待遇。他们或者变成小众歌手,个性独立,才艺双绝,像蕨类、兰花般在晦暗中不为大众所知。或者,为大众所知,并且与上一个时代近似,有着同样的折衷流行风,同样的有才气,或同样的品貌俱佳,却不会再成为人们欣赏回味再三的对象,其形象内涵也不再具有人文质感。在大众的眼中,他们更像是舞台秀场中的一具具声色玩偶,你来我往,你上我下,就是一场戏。
2009年6月11日
注:本篇资料来源:李皖《观察狼的二十种方式》,《回到歌唱》天津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满街都是寂寞的朋友吗?》、《在商业的齿轮里》,《听者有心》,三联书店1997年3月;《曾经与天一样高》,《五年顺流而下》南京大学2007年9月;《神迹降临1944年的秋天》,《倾听就是歌唱》四川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
首发于《读书》杂志2011年第10期